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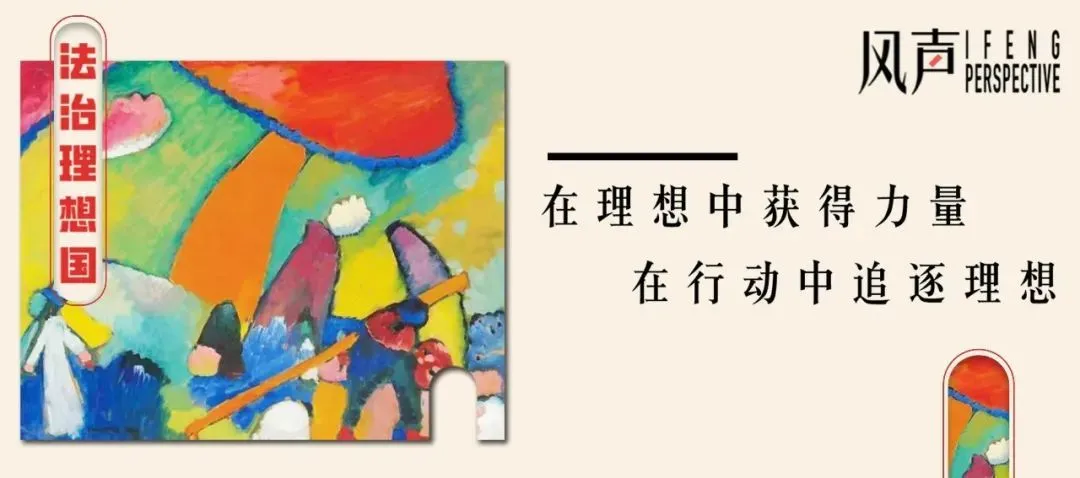
作者|赵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日,一起因“做法事”而被控诈骗的案件,在广东湛江市坡头区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称,陈某贵、陈某华在湛江市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并通过虚构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而骗取他人财物共计86800元。
庭审中,“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与“不做法事会使逝者魂不附体、影响子孙”等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成为控辩双方论证的焦点。而新闻采访也曝出,被控的陈某贵、陈某华祖上几代都从事“做法事”的行当,陈某贵更是已逾40多年。
本案一出即引发舆论哗然,毕竟仅因做法事就涉嫌刑事犯罪,多少都与公众的法感相悖。

“为逝者招魂超度”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吗?
《刑法》中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他人财物的数额以3000元为起点。这也说明,只要是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获利在3000元以上就已构成犯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诈骗者有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作出财产处分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了财产;诈骗者取得了财产,而被骗者则遭受了财产损失。
上述要件中,是否存在“诈骗行为”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诈骗行为又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前者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例如抠脚大汉冒充妙龄女郎以网恋为由骗取网友钱财;后者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即明知对方会陷入错误认识,自身也有告知义务,却隐瞒真相故意不告知。
本案的焦点也正在于:检方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贵以不做法事就会使逝者魂不附体、影响子女等为由,欺骗家属钱财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但辩方认为,老百姓付费“做法事”,并非笃信“做法事”就真能让逝者灵魂超度,或者不做法事就一定会有不利后果,而只是基于对逝者的缅怀和生者的安慰,完全属于带有民俗民风色彩的丧葬活动。
如果仅依据迄今已曝出的案件事实,即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也都表示并不完全相信封建迷信的说法。聘请被告人“做法事”,也只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市场交易,那么本案似乎就并不构成诈骗,因其欠缺当事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这一核心要件。
本案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也在于,封建迷信和民俗民风往往难以界分。有些活动和行为,即使最初带有迷信的色彩,伴随时间演进,也已成为民俗民风。如果将基于民俗民风的“封建迷信”活动都作为诈骗行为予以刑事打击,刑法就突破了其理应谨守的谦抑性。
然而,不是只要和民俗民风有关,就并不属于刑法打击的范围也并不一定。

翻阅裁判文书网,同样会发现借“算命”骗钱而被判处诈骗罪的案例。
典型的例如,2020年湖北省的王某了解到在网上给人算命、驱魔消灾可以赚钱,遂同有算命需求的李某联系。在知悉了李某的基本信息后,王某编造李某家庭命运不好,有前世鬼魂来讨债,需要做法事化解等事由,让李某为其转账4600元,之后又以李某姐姐的亡灵需要做法事化解,以及魂魄没有转回需要继续做法事等诸多理由,先后向李某索取了近2万余元。在该案中,法院就认为,王某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2021年的另一份判决中,被告林某同样在网上发布了算卦信息,而受害人葛某则被林某以需要做法事提升其运势为由,先后骗取了共计75900元。这起案件,同样以诈骗罪定罪量刑。
这几起案件的共性都在于,当事人所从事的都是做法事、驱魔消灾、算命等这类典型的封建迷信活动,而受害人也自愿为其封建迷信需求埋单,所差异的似乎只是,本案中的陈某贵世代都从事“做法事”的行当,这种职业化色彩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其欺骗性,也更容易被类比为寺庙里为人诵经超度的活动,因此似乎都已不再属于简单的封建迷信,而是具有了宗教化色彩。
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0条,“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如果在非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宗教事务部门会会同公安、民政、建设、教育、文化、旅游、文物等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并会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以及并处罚款等处罚。
如此来看,即使是有度牒的和尚尼姑做法事也需在指定场所进行,收取的费用同样按照《宗教事务条例》进行管理。

法律禁止非宗教教职人员做法事吗?
上述复杂背景,又引发出法律认定和处理上的很多难题:
其一,法律禁止非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诵经超度、做法事等行为吗?
其二,如果非宗教教职人员进行上述行为是否就一定属违法,若还以敛财为目的就一定构成诈骗?
其三,如果此类法事活动由“受害人”首先发出邀约而进行,“受害人”自己也笃信做法事可使逝者超度,甚至即使不是笃信也愿意遵从此类习俗以获得内心抚慰,是否就可豁免实施法事活动者的法律责任呢?
针对第一个问题。尽管《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活动原则上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但法律却并未明确禁止非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做法事等行为。但因为此类行为很容易就与封建迷信挂钩,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利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可以处以拘留、罚款等处罚”,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就会构成《刑法》中的诈骗。
由此来看,若只是单纯做法事,并未有“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甚至欺骗他人财产的结果,法律尽管不鼓励、不支持,似乎也并没有完全禁止。而不禁止,不将其直接归入违法行为的原因又在于,封建迷信总会和民俗民风相连,甚至常常攸关宗教信仰,若随便动用行政处罚和刑罚,就会出现国家干预信仰自由的问题。

针对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凭借朴素的法律直觉,如果法事活动甚至占卜算命、驱邪消灾都免费进行,当然不能被归于违法和犯罪,除非其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例如蛊惑他人服用有毒物品)。但若以敛财为目的,就极有可能会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实践中,为招揽生意、促成交易,做法事者一定会宣扬这种活动会驱魔消灾使逝者超度,但如此宣扬再加上收取他人钱财的结果,若以无神论的立场来看,极容易被归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即使是受害人自己也笃信法事有此功效,法事活动的收费也都是基于双方的意思自治而达成,也无法豁免做法事者的法律责任。
由此来看,即使我们最初看到这个案件会感觉与公民的朴素法感悖离,但深究下去也依旧会发现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也因为要件构成模糊复杂,做法事敛财是否就一律构成诈骗,在司法适用上也就丧失了确定性,也很容易就会落入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

公民有迷信的权利吗?
如果我们将国家对做法事者的惩戒都视为国家对个人免受封建迷信影响的保护,那么《刑法》适用的复杂就因为其背后存在一个始终悬而未决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公民有迷信的权利吗?即使公民为封建迷信所惑,从事一些愚昧未开化的行为,国家有干预的权力甚至义务吗?
如上文所述,封建迷信与民俗民风甚至是宗教信仰难以界分,而现代国家在此领域原则上又应秉持中立的立场。典型的,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在判决中宣告,“国家不得介入个人或宗教团体的信仰信念、信仰行为和信仰表现,支持或反对某种信仰是个人事务,而非国家事务”。
据此,国家在关涉宗教问题时需格外小心,其不仅不应优待特定信仰,更不能通过刑事打击排挤其他信仰;唯有国家首先履行此类尊重克制的消极义务,才能确保个人真正的信仰自由以及各种信仰的和平共处。
因为攸关个体的内心秩序和价值选择,即使某些宗教行为和民俗民风都带有迷信色彩,国家原则上也只能通过鼓励、指导、宣传、建议等柔性方式移风易俗,而不能轻易诉诸行政处罚甚至是刑罚予以强令禁止。
这是自由主义立场的体现。这种立场所确保的,首先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即便这个选择在一般大众不仅不理性,还愚昧至极。从这个意义上,个人有迷信的权利,国家并无权对迷信予以粗暴干预。
但是,自由总有边界。如果迷信活动会伤迷信者自己乃至他人至关重要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甚至危及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时,国家就不仅有权力甚至有义务予以干预。
典型的例如,在美国和欧洲都曾发生过不少父母因信仰极端宗教而拒绝对孩子进行医疗救助,进而被法院判刑的案例。此处体现的,就是国家基于对儿童利益的考虑,而对父母迷信行为的强势干预。尽管这种干预带有家父主义色彩,但本质上还是国家在个人的信仰自由和儿童的生命权之间进行的价值权衡。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裁判文书中出现的以做法事、驱魔消灾为由不断向当事人索要钱财而最终被判诈骗的案例。
事实上,实践中还有很多伪大师对信众进行威逼恐吓、辱骂要挟以获得巨额财产的案例,此类案件因为情节恶劣,不仅可能构成诈骗罪,甚至会构成敲诈勒索罪。

但,家父主义也有强弱之分,国家可在多大程度或者出现何种事由时,才应对个人的迷信权利和迷信活动予以干预,又是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议的背后仍旧是观念的不同,是到底更倾向于尊重个体选择,哪怕这一选择会造成危害后果,还是要对迷信行为进行纠偏的不同选择。也因为观念和选择几乎无法统一,也才会出现此类刑事案件司法的纷争。
去年曾有部爆款电影为《周处除三害》,其中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主人公在灵修堂对那些极端宗教信徒大开杀戒:陈桂林轻松的抬枪射击,一个个信徒应声倒地,但看似充满爽感的私刑处刑,却让人为其中的野蛮暴戾不寒而栗。
这些冥顽不化的信徒的确愚昧,但他们的生命就该这样被轻易剥夺吗?这个场景大概展现了对迷信者最可怖的处置方式,也警醒我们文明世界在面对迷信行为时复杂艰难的价值选择。但正因为复杂,法律工作者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就不能轻易得出罪或非罪的判断。
再回到本案,陈某贵、陈某华做法事是否真的就可被定为诈骗,恐怕目前还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也还有待法院更细致的调查甄别。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